近日,一段在高铁上播放的不文明行为宣传片引发热议。片中女士在高铁上录制自己的化妆视频,防晒霜和散粉洒在了邻座乘客的身上。不少网友认为,这种所谓的“不文明化妆行为”与事实不符,看似偶然发生,实际则是一种坚固的性别傲慢。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只是创作团队的一次失误,不应该上纲上线。
我们今天从这一事件说起,也结合近期其他的热点事件,聊一聊傲慢与愤怒的形变与转化。重点不是去评判对错是非,而是从这些事件出发,我们可以思考更多,行动更多。

高铁化妆视频截图
当李佳琦在直播间嘲讽消费者“不够努力”时,这份傲慢凭借的是其经济地位。它自然将引发受压迫群体的愤怒,然而,愤怒有什么用?被傲慢伤害了的我们是不是在无能狂怒呢?认识到愤怒的功能和意义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傲慢与愤怒的形变时常被忽视,比如《再见爱人3》中的情侣张硕和王睡睡的相处。
张硕在王睡睡生病时躲开,在两人相处中长期无视女方的感受和需求,而王睡睡却在准备礼物、照顾生病的张硕时尽心尽力。张硕看似温和无害,实则是在性别傲慢机制的庇护之下,被允许随意偷懒和逃避责任,作为伴侣的王睡睡当然有理由愤怒。但由于将女性作为关系维护者的社会期待,王睡睡的愤怒时常因为被解读为“委屈”而失去攻击性。

《再见爱人3》剧照。
傲慢时常被理解为一种性格特质,即个人习惯性将自己置于他人之上。然而,当傲慢升级为集体意识并形成制度,如厌女制度时,它会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设定规则来加固特定群体的特权,同时贬低和妖魔化其他群体。这种傲慢的权力结构不只作用于性别领域,它同样存在其他维度,较典型的是基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傲慢。
另一方面,当女性展示自己的愤怒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傲慢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往往会反扑,通过暴力或策略性的“倒打一耙”来维持自己的权威。然而,愤怒同时也可能会促进女性团结,激发大家站出来共同追求变革。此时,愤怒是导向仇恨的深渊还是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成为问题的关键。
作者|陈明哲
粗糙的傲慢?
一段包含“不文明化妆行为”的宣传片在全国范围的高铁上播放,因其体现了高铁运营公司的官方立场,所以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然而,在制作这样一部传播范围广、极具公共性的宣传片时,制作和审核团队都未能考虑女性经验,而是基于偏狭的刻板印象创作,且在审核流程中畅通无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误解、歧视和不屑一顾。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对女性“反自主”倾向的担忧。当女性习惯了被物化和嘲弄,并发现降低自尊后能够得到承认和善待,那么女性很可能将自身主动降格成令人愉快的物件,接受这些凝视。

引发争议的高铁化妆视频截图。
在常识中,我们会将傲慢理解为个人的一种性格特质。傲慢的人习惯于将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高于所有其他人,甚至无法理解他人的自主性。当这种傲慢不仅升格为一种集体意识,而且形成了制度时,它一方面会妖魔化某一特定群体的特质并借此贬低该群体,另一方面,被针对的群体却很难找到明确的加害者。厌女制度是一种系统的男性傲慢,它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设定厌女的规则以加固男性已有的特权。
凯特·曼恩(Kate Mann)在《不只是厌女》中认为,“厌女症”不应仅被理解为一种对女性的深层仇恨,它更是“用来监督和执行性别规范和期望的制度”[[1]]。在《应得的权利》中,她明确区分了“厌女”(misogyny)与“性别歧视”(sexism)。她认为,“性别歧视”是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分支,指那些自然化、合理化父权制规范和期望的思想;而“厌女”则像是“可电击狗项圈”,当女性破坏“法律和秩序”时,厌女制度通过惩戒女性来维持秩序。虽然“性别歧视”和“厌女”在概念上有所区分,这就意味着一个“清醒”的厌女者不一定歧视女性。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共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傲慢,对女性进行诋毁。

《应得的权利》,作者: [澳]凯特·曼恩 / 凯特·曼恩,译者: 章艳,版本: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5月
最初,为性别不平等和滥用辩护的是一种“粗糙的傲慢”,这一特质带着浮华的、扩张性的气场,与“男性比女性优越”的性别歧视信念相互加强。然而,与这种明显的傲慢相对照,那些厌女策略的执行者似乎只是单纯的自私,他们通过性别歧视让女性的真实感受和自主性被忽视。但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隐秘的“精致的傲慢”,这种傲慢冷酷且自私地置他人于不顾:我清楚男女都是人,但不妨碍我只看向自己,只有我配得这些权利。厌女者甚至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些制度,在女性为自己争取权益时,故意将她们视作无法言说的对象。
当然,傲慢中还包含着其他因素。比如李佳琦展现的傲慢还包含了他对经济上较弱势群体的无视与淡漠,这使他过于相信“努力即成功”的神话。一个社会越是鼓励竞争,强调地位和社会层级,傲慢的表现就越突出,傲慢者也更容易拥有手段和资源,将自身不公正的行为掩饰为合理的体面。这种现象反过来也意味着,个体越是傲慢,就越容易变得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区分愤怒之重
通常,“傲慢”往往以体面大度的悠闲模样出现,而被伤害者则表现得“面目可憎”。如前所述,当男性在面对“女人气”的日常行为,如化妆时,他们往往放任自己不切实际的想象,以男性眼光给这一行为指定意义。无论认为它是“琐碎、鸡毛蒜皮的”,还是“挑动欲望的”,都无视了女性的真实体验和女性自身对这件事的理解。但当女性对这种“傲慢”表达怒火时,结果往往有两种,她要么被视为小题大做、暴怒的扫兴者,要么被视为委屈的小女人。她们的愤怒总被曲解或直接无视了。
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其著作《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中,描述了前一种情况:女性主义者如何在提出问题时“变成了问题本身”。在一个和谐的家庭聚会中,当她突然察觉到对话中存在着问题并提出时,她如此不合时宜,破坏体面。她好像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她只是指出错误,就被认为是偏激、情绪激动的,这使她“成为了错误”,当她被视作敏感易怒的女性主义者时,错误本身反而消失了。事实上,她被人认为无端发怒才真正引发了她的愤怒。

《再见爱人3》剧照。
《再见爱人3》中张硕和王睡睡的关系提醒我们,男性傲慢与女性愤怒的形变时常被社会所忽视。如果男性从小到大都被灌输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天经地义拥有全部的“闲暇”,而女性就应当承担所有家务并照顾他们,那么这些男性就很难真正平等地对待女性。但在观察室嘉宾的点评中,王睡睡的愤怒却多次被解读为“委屈”,这揭示了女性在表达愤怒时所面临的困境。社会将维护家庭关系的责任锁定在女性身上,直白的愤怒可能有害于关系,因此对女性愤怒的解释使愤怒失去了原本的攻击性,“委屈”才更符合传统对女性的期待——温柔、被动和情感脆弱。
当女性展现愤怒时,还有一种常见结果:她们常常要面对维护男性傲慢的厌女制度的反击。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受到伤害的傲慢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感,可能会驱使他们通过暴力维护权威。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在面对社会变化时,往往会发动剧烈反扑——教训那些敢于为自己争取利益,忤逆男性需求的女人。
例如“非自愿独身者”(INCEL)运动就是一个反映。这个群体的男性成员,在两性关系中屡屡受挫,因而产生愤怒或忌妒。他们对于拒绝他们“应得的权利”的女性产生敌意,甚至对其使用身体或言语暴力。他们将两性关系看作一场男性之间征服女性的比赛,失败后将怒火全部发泄在女性身上。这种思维在对“偷拍”事件的网络回应中也有所反映。一部分男性被“偷拍举报”所激怒,通过策略性的“倒打一耙”,抓着男性被侵犯以及男性被诬告的几个个例有组织地进行反击,他们不关心如何解决“女性被偷拍”的普遍问题,也不关心男性受害者,他们不思考如何建立制度、保障受害者的权益,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他们想要的只是威胁愤怒的女性,维持自己压迫者的身份。[[2]]
在《好不愤怒》中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提到,大部分时候,愤怒往往会给女性带来高昂的代价,社会只对不造成危害的女性愤怒报以鼓励和欣赏。作者在分析美国政治时指出,当女性被假象蒙蔽,误以为自己取得了很大进展,她们就很容易主动放弃和被动丧失愤怒的权利。但幸运的是,当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女性被压制时,她的愤怒可能会激发无数女性站起来,共同追求变革。

《好不愤怒》,作者: [美国] 丽贝卡·特雷斯特,译者: 成思,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22年5月
明亮的怒火:“施行”促成“转化”
女性保持愤怒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愤怒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如果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寻求和解,而是追求报复性的胜利快感,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当前的很多事件中,愤怒似乎都发生了偏差。有时候,愤怒没能纠正现状的错误,而是用于指责“不够坚强”的受害者,并将这种针对受害者的攻击解释为“怒其不争”。以日本的头部娱乐公司杰尼斯为例,今年爆发了其社长喜多川针对旗下上百位艺人长达40年的性侵丑闻。但当这些受害者选择沉默时,他们却遭受了公众的指责和抵制。又或者,当有些女性被认为“不够女权”时,又出现了“媚男”“擦边”“婚驴”等新词对这些女性进行审判,这何尝不是背靠着新的话语权力,重复曾被女权主义批评的傲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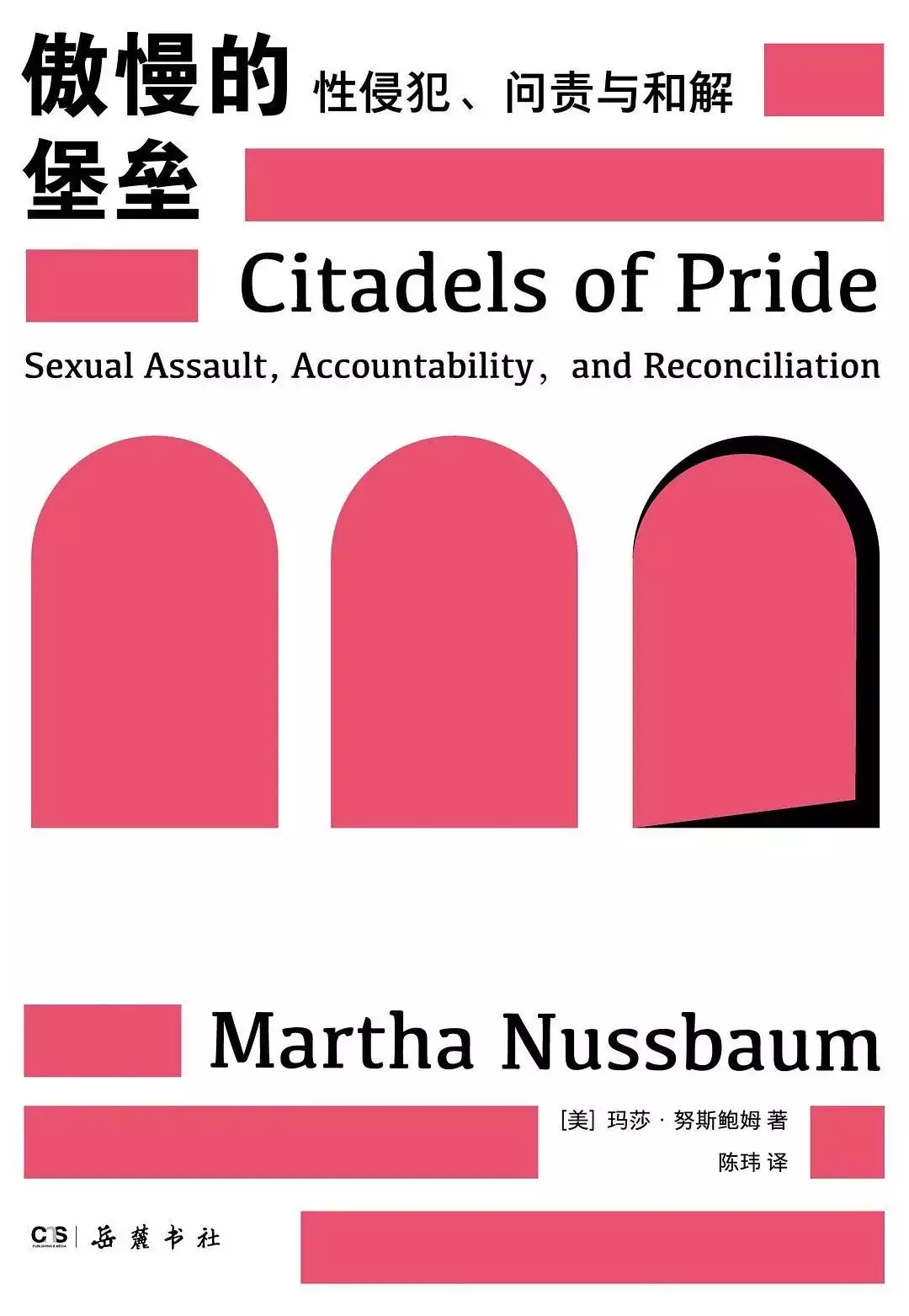
《傲慢的堡垒》作者:(美)玛莎·努斯鲍姆,译者:陈玮,浦睿文化丨岳麓书社2023年7月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傲慢的壁垒》中承认“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愤怒被想象成某种强烈的抗议,是逆来顺受的反面”,[[3]]也就是说,愤怒既强大又必要,它以激进的抵抗姿态标志出错误。但紧随其后的是,努斯鲍姆将“愤怒”一分为二:“报复性愤怒”和“转化性愤怒”(Transition-Anger),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面向未来”。努斯鲍姆认为,女性主义一直以来认同愤怒的根本重要性,但“当今的女性主义需要作出一个类似的区分”[[4]]。
“报复性愤怒”即“以牙还牙”,它是人在经历伤害后的自然反应——渴望回击,渴望加害者经历受害者经受过的一切痛苦。然而,倘若放纵人性的弱点,沉溺于报复主义,并不能修复过去的损伤,也无法许诺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同时,“报复性愤怒”还将腐蚀人格,造成沉重的心灵负担,灵魂停留在深渊之中。在热播韩剧《黑暗荣耀》中,被欺凌者文东恩不期待未来,只期待审判恶人和同归于尽。虽然文东恩的复仇实现了大快人心的法外正义,但我却痛心于她内在的死亡。在复仇之后,她的选择是自我了断[[5]],仇恨对良知的炙烤使她难以自洽。这一成功的复仇对现实生活中的受欺凌群体而言也不可复制。但文东恩的仇恨提醒了我们,弱势群体极端的“报复性愤怒”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缺乏退路。

《黑暗荣耀》文东恩剧照。
相对的,努斯鲍姆提出,“转化性愤怒”有助于女权主义团结。它超越了纯粹的情感回应,谨慎地绕开狂热和扭曲,驱动我们理性地分析问题,针对糟糕的现状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看向未来非常重要,这使惩戒成为一种变革,一种新的、正义规范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更有说服力的。在对未来的期许中,“转化性愤怒”给予人道德动力,它往往还带来团结和策略,使人倍感振奋。美剧《美国夫人》展现了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历史时期,“转化性愤怒”的力量。女性主义者们愤怒于女性缺乏平等自由的境况,于是通过群体性的抗议、游行、演讲、辩论、写作等多种行动争取社会变革。当然,愤怒有时也导致了女性群体内的分歧和冲突,如对同性恋、堕胎、家庭主妇等议题的不同立场和策略,但最终都为建立保障女性权益的社会结构而努力。
区分这两种愤怒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报复性愤怒”的价值,它往往是“转化性愤怒”的起点。对于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愤怒”不仅是瞬间的情绪反应,它更是在某一人生阶段中长期的、持续的态度,愤怒的情绪倾向在较长时段内拥有固定的模式。这两种愤怒状态反映了她们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心态。“报复性愤怒”不仅是心灵的阴影,也不仅会带来争端,同时也是理智探索的动力。每一位真诚的女性主义者都可能经历那个“充满怒火,想要报复”的阶段,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愤怒,她们能够对现状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和质疑。探索复仇的可能性过程也是她们不断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通过转化意识和交流,首先能促进的是愤怒的女性之间相互理解,这使差异终将转变为力量。“同伴之间的愤怒带来的是改变,而不是毁灭”[[6]]。
最重要的是,提出这两种愤怒的区分,实际上是为处于“报复性愤怒”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一种介入性帮助,唤起她们的“转化”意识。女性主义者通过习得“转化意识”,逐渐学会与自己的愤怒相处和搁置仇恨,以及理解不同女性群体的愤怒,由此得以走向更积极的“转化性愤怒”状态。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保持愤怒,期待光明。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明哲;编辑:走走;校对:卢茜。封面图片为《将来的事》(Lavenir,2016)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